养老院发展需要资金
竟然向老人伸手
她把毕生积蓄40万
借给了养老院
身患重病无钱医治
纵身一跳
结束了花甲生命
而借钱给养老院的
不仅仅是她自己
……
7月31日是孙带弟的64岁生日。儿子说,虽然母亲患病在医院治疗,但自己本来打算给她买个生日蛋糕,给病痛中的母亲“营造点喜庆气氛”。
孙带弟没有等到庆生的蛋糕。7月25日,她跳楼身亡。在老人的遗物中,家属找到了她和“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负责人于某签订的一份借款协议。孙带弟生前住在这家养老院。2017年,她以年息4.8万元的条件,将毕生积蓄40万元借给于某。在孙带弟轻生前不久,她还多次通过微信等方式向于某催要这笔借款,用于偿还住院期间所欠债务。无果。在她身故后,于某向家属承诺“凑点钱”,先给孙带弟支付火化、购买墓地等丧葬费用。还要从借款本金中扣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孙带弟之外,还有多位老人向这家养老院及于某出借了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的款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迈多病;曾经在养老院入住;曾被承诺高利息;至今难以拿回借出的本金。留在他们手里的,是一份份难以兑现的“借款协议”。
病痛中的孙带弟没有等到64岁生日。
01 40万借款无法要回
出事之前,身患癌症的孙带弟已经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她的癌症尚在早期,医生说有治愈的希望。”孙带弟的儿子小丛说。
但治病需要钱。小丛说,母亲在出事之前,一直在为钱的事儿闹心。64岁的孙带弟离婚多年,唯一的儿子小丛经济条件一般。2017年,她曾搬进位于大连甘井子区的一家养老院,托费不高,但却“耗尽”了她的积蓄。
按照小丛的说法,这笔钱是被母亲借给了养老院。在小丛提供的一份手写借款协议中记者看到了如下内容:“甲方于某向乙方孙带弟借款40万元,转账谭某账户,借期五年,到2022年3月3日。月打息4000元,年息48000元。每月5日转息4000元加工资1000元。合计5000元。免费提供松江路住房一套,水一吨,电20度,余下的自理。”在这份借款协议中还写明:到息日不能超过3天,超过3天就算违约,乙方有权收回40万投资,解除合同。合同落款为于某。同时还盖有“大连市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的公章和谭某的私章。
小丛解释说,“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是母亲生前曾居住的养老院。借款人于某是该养老院的负责人。“我母亲入住养老院不到一年,于某就找到她,说养老院继续发展需要资金,希望她能借点钱。”小丛说,因为当时母亲身体还硬朗,能在养老院干点零活儿。于是除了承诺的4000元月息外,于某还许以1000元的“兼职工资”以及免费居住的该养老院松江路院区一个房间(即协议中提及的“免费松江路住房”)。按照这份协议,孙带弟满心期望能在养老院过上“按月领息”“免费居住”的好日子。
但好景不长。2019年8月,月付利息终止了。按照孙带弟对儿子的转述,此后她曾多次和于某协商,要求按协议条款收回投资解除合同,但一直未获对方同意。在她和养老院经理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记者看到,7月15日,孙带弟还曾求于某还钱:昨天晚上儿子儿媳,二妹小妹给凑了1万块钱,现在(医药费)还剩1万多块钱,你想想办法给我凑几个钱吧,凑一点儿是一点吧,没有办法了。
于某的回答是:我真的太难了,疫情影响,都不能过了。“这暂时的困难呢,大伙儿帮着度过度过,你自己先颠倒一点钱,再过一两天就好了。”在两人此前的聊天中,于某曾称,孙带弟已经在养老院住了6年,每年3万元的托费都没有交,加在一起已经18万,让孙带弟“感恩吧”。他还曾让孙带弟“您去法院起诉吧”“我已经有那么多官司,也不差你一个。”
孙带弟终究没有“颠倒”过这难熬的日子。十天后,她跳楼身亡。
02 多位老人借款
孙带弟并不是唯一借款的老人。
80岁的王淑娟老人和老伴都曾是“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的养员。她说,自己不愿给儿女造成负担,于是和老伴于2018年一起入住“阳光花园”。入住第二个月,经理于某开始向自己借钱,理由是“养老院需要装修”,并许诺了12%的年化利息。
考虑到自己住在养老院内,也为了拿到不菲的利息,王淑娟将4万元钱借给了于某。她说,此后于某又先后多次开口借钱,理由都是“养老院建设需要”。老人和养老院签订的借款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年利率12%,按月付息,最后一个月本息一并还清。
如果到期不还款,王淑娟有权不缴纳费用继续居住,且有权收取其他养员的费用冲抵借款。“我一共借给养老院十万元。当时就当作投资了。”王淑娟老人说,支付了约3个月利息,“投资生意”就断流了。从当年8月份她和老伴搬离这家养老院至今,10万元借款她只收回1.4万元。为此她还将养老院和于某告上了法院。2020年7月24日,甘井子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养老院及于某需向王淑娟老人偿还借款8.6万元及利息。
此案很快进入执行程序。2021年5月3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下达的(2020)辽0211执6966号执行裁定书显示:由于被执行人阳光花园养老院及于某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执行程序。虽然养老院法人及于某已被“限高”,但王淑娟还是没能拿回自己的积蓄。
71岁的侯淑贞老人情况也类似。她说,自己2017年在阳光花园养老院的金州龙王庙分店居住,于某以“姚家店锅炉损坏,需要维修”的理由,分5次向自己借款14万元,同样承诺12%年化利息。至今本金仍未拿回。而曾在该养老院居住的老人王大山目前已经去世。他的儿子说,2016年到2017年间,父亲也曾以年化12%的利息借款30万元给养老院,但直到父亲去世,钱仍未还。
“我们没和养老院打官司。就算官司赢了,钱也拿不回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王大山的儿子声音中略带疲惫。
03 官司累累
“官司赢了也拿不回钱”的叹息并非杞人忧天。
记者梳理发现,2020年至今,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及于某涉及多宗民间借贷纠纷诉讼,均系被告。原告中有王淑娟、侯淑贞这样,曾经在养老院住过的“债主”;也有如王大山一样已经去世的老人,由其继承人发起债权诉讼。
这些原告老人的共同特点是:年龄多在70岁以上;养老院承诺的借款年化利息高达12%;多次讨要无果无奈起诉。法院判决结果,也均为原告胜诉,养老院、养老院法人及于某等需偿还债务本息。
但胜诉方多数面临和王淑娟老人一样的窘境: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程序暂告终结。
记者调查发现,涉及这一系列借款诉讼案的养老院分别为“大连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及“大连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
其中“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于2016年、2017年两次变更投资人。原投资人谭某退出。但谭某目前还同时担任“甘井子区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的负责人及大连金州区花园阳光养老院有限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经理。她也成为多起诉讼案中的被告之一。这一系列诉讼案中的另一被告、主要借款人于某,并未出现在上述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登记名单中。由于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于某谭某均被多次限制高消费,于某还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
一系列借款诉讼,均为几乎雷同的操作模式。这不禁让小丛心生疑虑:“借款对象都是我母亲这样年迈、多病、缺乏法律常识和风险意识的老年人。还钱时一拖再拖。养老院耗得起、欠债的耗得起。但这些年迈的老人债主们耗得起吗?”
04 借款人回应
8月7日、8日两天,记者多次拨打于某的手机,最终于8日中午联系到他。
于某告诉记者,孙带弟确实与他有借款协议。但他强调,借款合同“没有到期”。“我们会按照合同文本,依法依规处理后续问题。”于某称,但考虑到孙带弟在院期间,双方关系“处的不错”。养老院可以从其借款的本金中“预支”给家属一部分,用于购买墓地或支付丧葬费用。
至于他本人和养老院涉及的其他民间借贷纠纷,于某表示,目前养老院还在正常经营,不会不还钱。“受到疫情影响,我们暂时没有偿还能力。但养老院还在尽力维持运转,会按照借款合同以及法院判决文书,执行判决。”
记者还联系了“阳光花园养老院姚家店”的工商登记负责人谭某。但其手机或处于关机状态,或无人接听。记者发去短信表达采访意愿,但截至发稿前未获回应。
发稿前记者从小丛处获得了一份通话录音。这是8月7日下午谭某在收到记者短信后与小丛的通话。通话中她称:“老于(指于某)不是已经和你们沟通了吗?最晚周一(8月9日)我们先凑钱给你妈把墓地买上,现在最重要的是入土为安......你让记者曝光,那我们就没法再谈了......”小丛说,目前母亲还欠着朋友和亲属的几万元钱,欠医院2万余元医药费。而她借给别人的40万元,不知何时才能拿回来。
王淑娟则在看着她和孙带弟的微信聊天记录发呆。这些曾借款给养老院的老人们会在手机上互通信息,交流“要账”的新进展。2021年5月末,孙带弟曾经向她咨询过起诉养老院的详细事宜。“当时她说自己得了大病,怕撑不下去了。”王淑娟很后悔自己没有多劝劝这个“老妹子”。“如果她能像我一样去起诉养老院和于某,可能也不会选择走这一步.....”而当问及她觉得什么时候能拿回钱时,王淑娟语塞了。
“我都80岁了,可能等不到了。”许久后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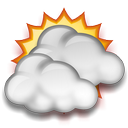 23℃~29℃ 多云
23℃~29℃ 多云 